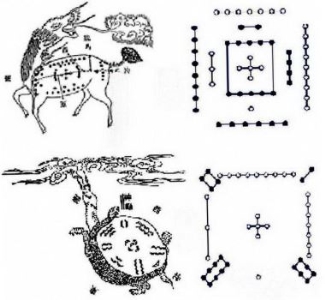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向天下发布平倭诏,历时七年的万历援朝之役正式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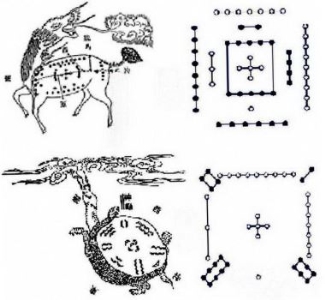
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
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
——平倭诏 万历援朝之役,大明前后征调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等镇将士十九万五千七百人,损失八万五千余人,粮饷、米豆、兵器、盔甲、火药等耗费合银两千四百多万两。
以此为代价,大明成功的在东亚栽下了一棵稳定之,确立了东亚地区三百年的和平局面。
但是,栽下了这棵树的大明非但没有从中受益,反而还在四十多年后走向了。
结果,真正在这棵的大树下乘凉的不是大明而是。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大明栽的树却让清朝乘了凉?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万历援朝之役对大明和李朝造成的影响都有哪些。

扼杀了大明的萌芽 元贞元年(1295年),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黄道婆从崖州返回故乡——松江府乌泥泾镇,她在崖州时改良的纺车、织机等工具和发明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随即在以松江、苏州、杭州为核心的三吴地区推广开来。
得益于黄道婆推广的工具和技术,三吴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发展的十分迅速,尤其是大明建立后,由于“三吴地区赋役之重,甲于天下”,使得大量农民被迫放弃田地转而从事棉纺织业,三吴地区的棉纺织业迎来了空前发展。
隆庆、万历时期,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积累,三吴地区出现了大量拥有资产在三十万两白银以上的棉纺织业工厂主,在田地大都被大官僚、大地主兼并的情况下,工厂主们只能将资产用于扩大生产和招募工人,这样,三吴地区就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为了缓解万历援朝之役后出现的“国用匮乏”,明神宗派出了大量宦官对三吴地区的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征收重税。
这种情况下,大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了。
严重削弱了大明的辽东军力 万历援朝之役中,大明从临近李朝的辽东抽调了大量将士,其中有杨元、李宁等名将和赖以抵御土蛮和女真诸部的两千家丁和两万选锋军,结果随着碧蹄馆之战、南原之战和泗川之战的失利,杨元被杀、李宁阵亡,家丁和选锋军损失殆尽。
癸巳(1593 年),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殄在迩,不与他兵分其功。
潜率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馆,遇伏一举歼焉。
其家丁李友升者,积劳已至副总兵,只身殿后战殁,如松始得脱。

——《万历野获编》 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了李成梁在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时毫无作为、还导致了乘机不断发展壮大。
使得李朝丧失了遏制女真发展的能力 万历援朝之役爆发前,李朝拥有战兵十七万两千四百人,至万历二十六年明军与李朝军队向发动反击时,李朝的战兵竟然下降到了两万五千人。
这种情况下,原本对女真拥有强大控制力的李朝失去了扼制女真发展的能力。
在大明的辽东军力被严重削弱和李朝丧失了扼制女真发展的能力后,努尔哈赤乘机不断发展壮大,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灭哈达部,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建都赫图阿拉,万历三十四年,喀尔喀五部尊努尔哈赤为汗,万历三十五年,努尔哈赤灭辉发部,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灭乌拉部,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建立制度,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于中大败明军。
此后直至率入关定鼎天下,清朝都在大明所栽的那棵大树下毫无任何后顾之忧,并且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大明在“国用匮乏”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进而没有足够的财力应对努尔哈赤的发展壮大,所以说,大明在万历援朝之役中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栽的树最后却被清朝乘了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明朝的万历帝王到底是明君还是昏君呢?看完这个就明白了
大明每年农税二百万两白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影响,天子每年都要免除大量的农税并赈灾,他先是下令赈灾款从内库出,然后就是战争特别费从内库出,接着是修河治水钱也要内库出,还有军屯歉收也要内库补助等。 为了应付各种开支,万历就挖空心思地挣钱。他除去收了近三百万两海税银和上千万两的工商盐茶银以处,还下令开放书局给内库挣银子,只要能卖出去的书一律刊印,或者只要肯交钱就给你印。 所以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书籍刊印得最多的时代,闻香教徐鸿儒的经书都是皇家书局刊印的,闻香教的作乱宣传单也是皇家书局印的--就因为徐鸿儒付钱了…… 北京的路人穿的衣服也是,这一切也是为了税收上的考虑。曾经有言官痛心疾首地谈到大明的百姓穿的比官员还漂亮,更有人开始穿明黄色的衣料了。文臣要整肃朝纲,不许百姓僭越,一开始万历也曾犹豫过,但收绢税和花布税的问他: 如果不许小民穿绫罗绸缎,那万岁爷找谁收税去呢? 最后就是万历一辈子再次倒在了银弹攻势下,顶住了文官的齐声痛骂,把大明祖制给修改了,废除了所有关于车马、衣服和轿子的限制。 万历朝十年后,地球进入小冰河时期,在连绵不断的天灾面前,为大明积攒下的国库储蓄迅速地耗尽了。虽然南方各军镇吃饱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朝廷拨给救济款,但随着灾害地持续,万历皇帝渐渐感到他无力维持大明水师的开销了,所以就允许沿海各军镇自行向海商收取一定的海税,作为水师的维持费和清剿海盗的费用。 这个政策推行以后,大明水师就进入了不稳定的发展期,有地军镇经营不善,税收很高但海盗仍然猖獗,导致附近的海商贸易萎缩,并进一步导致所属的水师急剧退化。相反,经营良好的军镇则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海上武力,从而能够制造出更大地海贸安全区,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到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大明水师驱逐了盘踞在澎湖一带的荷兰人。当时万历皇帝为了进一步给内库开源,甚至制定了渡海进攻马尼拉地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万历皇帝听到了当时盛传于中国的一种谣言,那就是;马六甲一代盛产黄金和白银。 万历三十六年后,万历皇帝还曾派了几拨太监前往那里进行实地考察,其用意之险恶不问可知。只是那些太监带回的事实粉碎了谣言,万历皇帝确认了金山、银山的说法为子虚乌有后,才讪讪放弃了侵略企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万历帝王是如何幸免一场文字狱的?
自古文人容易惹祸。 有的人是,文人一般是祸从笔出,比如年间著名大儒吕坤。 这人本来是山西按察使,干的是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监督、考查以及检举的工作,可他却喜欢“”,在职期间不好好干他的本职工作,却去搜集什么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然后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的书。 想必写得不错,连宦官陈矩都爱看,出宫时在书店看到了,也买了一本带回宫里,不幸被看到了。 为什么说不幸呢?因为郑贵妃看到后,麻烦事便接踵而至。 郑贵妃一看,这书不错啊,但还有点,还可以更好,便叫人增补了十二个人——关键是,她把自己的“事迹”增补了进去,而且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 很明显,她想借这本书抬高自己的地位。 人家吕坤收集的,可是历史上的贤妇烈女,就算她是这样的女人,但也不是历史上的这种女人,但是她不管。 这叫有权任性。 有权不任性,要权有屁用! 做了这些事情后,郑贵妃又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一个版本,这样一来,《闺范图说》就有了两个版本,经常被人混淆。 这是万历十八年发生的事,一直到万历二十六年,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没事。 再说了,这是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材料,是号召妇女们向史上那些好女人学习的书,又不是黑材料。 但还是出事了。 事情出在万历二十六年五月。那时的吕坤,已是刑部侍郎,他给皇上大人上了一道疏,名叫《天下安危疏》,请做两件事情,一是节省费用,二是停止横征暴敛。 这是好事啊,有大臣忧国忧民,提醒皇上不要走偏,是好事啊,人也是好人啊。 你要做好人,有人偏不让你做好人,自古以来都不乏这种人。 不让吕坤做好人的人,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不知他是与吕坤有仇呢,还是想借此立个功,积累往上爬的资本,反正吕坤的上疏,让他逮着了机会,他便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现在又上什么安危疏,显然没安好心嘛,尤其是之前那本《闺范图说》,很明显是想拍郑贵妃马屁嘛——“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 戴士衡所说的那本《闺范图说》,显然是指郑贵妃指使人重新刊刻的那本,不是吕坤的原著。 吕坤不想平白无故蒙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皇上明鉴,我写的不是这本,请皇上让人一一对照,我写的真的不是这本;有人说是我写的,有包藏祸心之嫌。 皇上大人不想追究,因为事情牵涉到郑贵妃,他不想因为一本破书,而搞得家庭不和,便装聋作哑,你们爱闹就闹去吧,不信能闹翻天。 这两位倒是不闹了,却有其他人唯恐天下不乱——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家伙,估计是吃饱了没事干,需要找点事消消食,便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名叫《忧危竑议》的跋文,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到处散发。 实际上,“朱东吉”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是写这篇跋文的人,杜撰的一个名字,取的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的意思。 这篇跋文一问世,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石头,因为按照它的分析,吕坤写《闺范图说》的目的,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之位埋伏笔。 跋文还说,吕坤的“安危疏”,为什么要专门讨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呢?这是影射“国本”问题啊——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 更恶毒的是,跋文地指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一出,举世哗然,很多人不明真相,纷纷指责吕坤,原来这人包藏祸心啊,还大儒呢。 吕坤又忧又怕,借口生病辞了职,回家避难去了。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虽然也很恼怒,但冷静一想,我若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再继续“顺藤摸瓜”,对相关人员一一进行处理,势必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到时候连郑贵妃和她家人都跑不脱。 他若这样做了,历史肯定会重重地将他记上一笔——瞧啊,咱们的万历,也会搞。 这样的“名垂青史”,他可不想要。 这样一想,他便感觉,亲下谕旨说,你们别闹了,《闺范》一书,是朕赐给郑贵妃的——她是朕的爱妃,难道朕送本书给她都不行吗? 至于的戴士衡对吕坤的弹劾,实属诬告,不处理肯定不行,还有全椒知县樊玉衡,在戴士衡上疏之前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也是唯恐天下不乱,这两人,很可能搞事情,《忧危竑议》也可能是他们写的,樊玉衡不处理也不行,便把这两人抓来审问,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罪名,分别发配广东雷州和廉州。 至于吕坤,他本来是冤枉的,而且已患病致仕,就别管他了,随他去吧。 那以后,吕坤再也没有当过官,一心在家闭门著述、讲学,又活了二十年,其主要作品包括《实政录》、《夜气铭》、《招良心诗》、《呻吟语》、《去伪斋集》等十多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水利、教育、音韵、医学等各个方面,成为明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思想价值日久弥新,至今仍在闪闪发光,不仅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影响重大,而且在日本、美国、韩国、 哥伦比亚、埃及等国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其家乡河南宁陵县,还曾于2006年召开吕坤思想研究专题座谈会。 不知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吕坤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不会感谢那些,给了他“因祸得福”机会的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