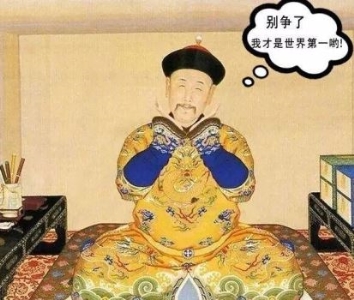韩瑗,字伯玉,时期宰相,尚书韩仲良之子。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韩瑗出身于南阳,历任兵部侍郎、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侍中,袭封颍川县公。
他在废后之争时,支持、褚遂良,反对,引起武则天的嫉恨。
显庆二年(657年),韩瑗被诬陷谋反,贬为振州刺史。
显庆四年(659年),韩瑗病逝,又被抄没家产。
中宗年间平反。
后追谥“贞烈”。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韩瑗年轻时操行出众,,且通晓吏治,贞观年间累迁至兵部侍郎,袭爵颍川县公。
担任宰相 永徽三年(652年),韩瑗升任黄门侍郎。
永徽四年(653年),任命韩瑗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后又加其为银青光禄大夫。
永徽六年(655年),韩瑗进拜侍中,兼任太子宾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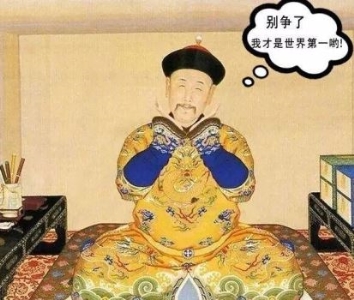
当时,唐高宗欲废黜,改立武则天,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极力反对。
韩瑗也痛哭进谏:“皇后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如今无罪却要被废,这不是社稷之福。
”唐高宗不听。
次日,韩瑗再次进谏:“匹夫尚且知道挑选媳妇,何况天子?《》有云:‘赫赫,灭之。
’臣每次读到此处,都要掩卷叹息,不想今日竟亲眼见证这种灾祸。
”高宗大怒,命人将韩瑗拉出大殿。
武则天最终还是被立为皇后。
显庆元年(656年),韩瑗上表高宗,为贬任潭州都督的褚遂良讼冤,称褚遂良“公忠体国”,希望高宗将其赦免。
高宗道:“褚遂良狂悖乖张,直言犯上,朕责罚他,怎算有过错呢?”韩瑗答道:“褚遂良是国家重臣,他的缺点就好像白纸上停了一只苍蝇,何至于就说是有罪呢?陛下富有四海,安享太平,却驱逐旧臣,难道您还不醒悟吗?”高宗不听。
韩瑗忧愤不已,请求辞官归田,高宗没有批复。
贬死振州 显庆二年(657年),许敬宗、秉承武则天的意旨,诬奏韩瑗勾结褚遂良(已改任桂州都督),。

许敬宗奏称:“韩瑗认为桂州乃是用武之地,准备以桂州作为造反策源地,以褚遂良为日后起事的外援,因此行使宰相职权,授褚遂良为桂州都督。
”高宗因此将韩瑗贬为振州刺史,并命终身不许回京,又将褚遂良贬为爱州刺史。
显庆四年(659年),韩瑗在振州病逝,时年五十四岁。
这时,许敬宗又诬称长孙无忌谋反,并奏称:”长孙无忌谋逆,都是因褚遂良、柳奭、韩瑗挑拨煽动而成。
“唐高宗遂将长孙无忌流徙黔州,追削褚遂良官爵,并将韩瑗、柳奭除名。
同年七月,唐高宗遣御史前往振州将韩瑗押解回京,并命当地州县抄没其家产,随即又命将其就地处死。
御史到达振州后,方知韩瑗已死,便开棺验尸,又将韩家近亲全部流放岭南为奴婢。
神龙元年(705年),遵照武则天遗命,追复韩瑗官爵,并赦免其亲属。
后追谥“贞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李裹儿拥有唐朝第一美人之称 却为人骄纵
此页面是否是列表页或首页?未找到合适正文内容。
清朝时期有一人贪得比和珅还多,手握兵权排第一
就史笔与史论来说,长期以来,晚清史学者们愿意把清末大贪官庆亲王奕劻和中期朝的大贪官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庆亲王奕劻之贪,在一个皇朝行将结束的时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摧毁性作用;而和珅之贪,史论常把它和由“”转衰,即由乾隆朝“盛世”到朝渐衰的结节点连在一起。且不论这种史论判断是否带有史笔史论者个人的情感因素,常识告诉我们,个人的贪,与体制内的贪,一定存在着共同体的关联作用。任何事情表现为个体行为,是古旧认识论留给中国后人的认知缺陷。清史揭示,和珅之贪,没有个人“好物”贪欲作为推手和庇护,是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的,--和珅是常在乾隆皇帝这条贪之河边走而湿了脚的那么一个大贪官(史料记载,乾隆常借各种名义叫臣下百官孝敬他)。同样,清末庆亲王贪的基础,就是整个晚清官僚体系的腐败。由此说明,史学者们愿意把这两人作为典型大贪官,既在贬斥旧官吏的贪劣,更具有渐衰和皇朝没落这种以史为鉴的政治因素。 其实,在确认以上两人是清朝最大贪官(之一)的前提下,清朝还有一个大贪官,这便是晚清鼎鼎有名的。或者说,封建专制政权下的贪官,只有之一,没有之最。 当时一位叫瓦伦丁.吉尔乐爵士的外国学者对李鸿章及他的洋务事业有过深刻的研究,他在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洋务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写道: “在李鸿章的朋友和亲戚中间,腐败以最大和最无耻的嘴脸出现,并规模很大地扩展开来,于是这些人就在社会上追随着他,在政治上支持着他。对于这种现状,纵然是那些对他予以赞扬的人也不可否认地看到,他凭借着自己拥有的巨大的财富而著称于世,所以,对于他本人的双手是干净的这一点,我们没法确信。据说,倘若要找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么此人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经济转型(农耕到工商)和改革(近代化)的主要枢臣。这位著名的、后人一直争议不断的晚清改革家,利用洋务购买和本国应用的渠道,上下其手大敛其财,在垄断权力资源的同时,又垄断了经济资源。但这里必须指出,皇朝时代为官之贪,只要不是个人欲壑难填,在为官为政个人贪欲的同时,又能带动体制内一批人先富起来,是符合当时的为官之道的(经手人可以收受回扣甚至虚报,然后某一小集团共同分利)。这样的史料,在中古及近古的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确是不胜枚举。个人贪欲是人品的瑕疵,为官而又对至尊个人或整个集团的忠,才是是否可以为官、为大官的最高道德标准(忠孝仁义礼智信,把“忠”列于首位)。贪官在历史民间舆论上处于的道德最底层,但在官僚体制内并非如此。这是专制皇朝社会的两种道德评判标准。 按晚清西方人对对清朝官僚体系的认知是,“官僚的权力应该包括盗用公款,作为其一种阶级特权,被人们接受着”。而关于李鸿章的一个显著例证是:“到了1894年底,当厄运即将降临到李鸿章头上的时候,社会上盛传在他的一个儿子的负责下,他的可移动资产被偷偷地往南运回了自己的老家安徽,那就是整整一船的大箱子、板条箱、盒子和袋子,就如同在1901年暂居外地后回到北京时带回一火车值钱的东西一样”。就在同一时期,“宰相合肥天下瘦”的传言,决非空穴来风。据嘉庆朝的上谕、参与和珅抄家臣僚的奏折、内务府的折片等金额数字加起来,和珅贪污的家产总数不会超过4000万两(以亿数为传统政治因素控制的民间传说),更保守估计为1000万两;而晚清李鸿章的动产与不动产总额,就保守估计已超4000万两。有史学研究者明确指出:“李鸿章的家产已经超过了和珅”--晚清工商化即洋务运动也决定了社会总财富必然超过前代。 封建宗法官僚(权力至尊与权力崇拜)制度培植出的贪官,从来没有“之最”,只有“之一”。李鸿章与前两者的最大区别是,他没有倒在同一朝代内部整治即吏治的反腐浪潮中,而是倒在了持之以恒的洋务(近代化)事业和孜孜以求挽救没落皇朝的工作岗位上,即他个人吸引眼球的“亮点”不在贪上。这足以使他成为后人评说中的“有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