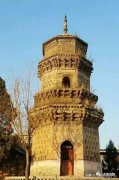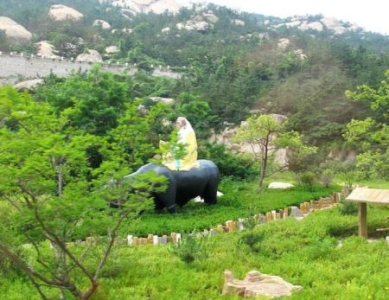解析真实的秦始皇嬴政:“焚书坑儒”是弥天大谎
褒之者认为他统一了天下,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等,功大于过。

贬之者则认为他阴险、残忍、暴虐。
网络配图 如此残暴的君主,似乎在他的专制统治下发生过的一切残暴血腥之事都不足为奇,诸如历史上着名的“”事件,那是在秦始皇一生中永不可抹掉的污点。
秦始皇一直为后人诟骂,甚至连长相也被描述得极其阴险——“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但以常理而言,这种长相可能跟他少年时期在赵国颠沛流离,营养不良有关。
秦始皇被世人误解的,不只是他的长相而已,还有他的真实为人。
秦始皇曾有“禅让”的念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用新的帝号,自称,并规定继任者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
这是《》所记载的。
但是自西汉起,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起初秦始皇曾经有过要用禅让制传位的念头。
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乖张、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扯不上边。
然而,近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说法,因为确实有史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西汉所着《说苑·至公》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议国家政权交接的事,他说:“古代有五帝禅让,又有三王代代相传,你们认为哪一种更好?我想采用最好的方法。
”在场的博士都不说话,只有鲍白令之回答说:“如果以天下为公,就会禅位给贤能者;如果把天下当私家财产,则会在家族内代代相传。
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
” 秦始皇帝仰天而叹道:“我的德性可比五帝,我将让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谁能接替我呢?”鲍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说:“陛下行的是夏、商纣之道,却想学五帝让位于贤者,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
” 泰始皇帝闻听此言大怒,道:“令之你往前站!你凭什么说我行桀、纣之道?如果说得通则罢了,如果说不通你就别想活了。
”令之地说:“陛下你,后宫女人数百,倡优过千。
为了自己的享受,耗尽天下民力。
你还偏驳自私,不能推己及人。
陛下你还说自己的功德压过一切君主。
以你这样的德性怎么能和五帝比,你又怎么有资格管天下呢?” 一席话说得始皇面有惭色,过了很久才说:“令之所言,是让我当众出丑啊。
”于是罢谋,自此再也不提禅让了。
在上面这段话中,秦始皇起初自比于五帝,打算仿效他们以禅让的形式传递王位。
“五帝”在历史上有三种常见说法,一是、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见《世本》;第二种说法是太白皋、、黄帝、少白皋、颛顼——见《礼记·月令》;第三种说法是、颛顼、高辛、唐尧、虞舜——见孔安国《尚书序》。
在历史上被奉为德性的最高典范,当时参加会议的博士们可能都认为秦始皇比不上五帝,又不敢说,于是集体沉默,只有鲍白令之出言将秦始皇斥责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来的想法而“无禅意”。
对于《说苑》中的这段记载,过去人们一般都不大相信,大概是因为人们对《史记》的绝对信任。
此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而《史记》不记的内容,后世学者们往往会不予以承认。
再说,说那个赫赫有名的专制暴君秦始皇有禅让思想,像是天方夜谭。
所以《说苑·至公》的这段材料,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重视。
然而,我们若将《说苑》中的这段资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内容相对照的话,就可以发现,两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
而且,按照当时的客观事实,此事也是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博士议政的说法一致。
秦始皇时期曾设置很多博士官以充当顾问。
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实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们或臣僚们加以讨论,最后由秦始皇斟酌参考,决定是否执行。
用什么方式传王位是有关秦王朝当局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们来议论—番。
这一点在《说苑》和《史记》中都有记载。
只是接下来,两本书有了分歧,《说苑》提出“禅让”的说法,但没有了下文,而《史记》则根本没有“禅让”的记载。
联系到秦始皇后来“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打算,人们选择相信《史记》。
不过,看历史不应该只看一家所言。
《史记》本身孤证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为评判其他史书的标准难免有失偏颇。
网络配图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让后人对《说苑》的记载产生怀疑,那就是,《说苑》的作者刘向是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禅让”的。
当时刘向为了给王莽篡位造势,不惜篡改前史,特意制造了新五行学说,这种行为难免让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也会自然地想到刘向这段文字是为王莽造势用的。
实际上,秦始皇有禅让思想是有可能的。
战国时曾一度流行“让贤”说,很多人不但深信尧舜禅让是真事,而且还有人效而行之。
曾打算让位给惠施、想要让位给,燕王哙则是真真实实地让位给予之。
虽说“禅让”之说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国向来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统治者也难免受到影响。
秦始皇成功地统一全国,认为自己的功德足以压倒一切帝王,应该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在一个高度,所以极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
这或许只是作秀,却是有可能发生的。
刘向虽然有过劣迹,但《说苑》中的记载也不可能完成是的荒诞之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苑·至公》中这篇记载可以作为《史记》的补充资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那么,如此有参考价值且甚为重要的材料为什么会长期被人们忽视和否认呢?总结一下,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尧舜历来是人君的典范,而秦始皇则向来是被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残暴、苛政耳闻目见,认为秦始皇不配与尧舜相提并论,因此不愿意讲述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史料难免不完善。
是汉初人,一来不能免俗,二来作为治史严谨的他,在资料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记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们对《史记》的可靠性过分迷信。
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
一流学者、史学家班固在所着的《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这基本上是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态度。
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多见于《史记》,其他的书籍记载甚少。
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部分内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最高标准。
其三,人们对《说苑》的史料价值认识不够。
《说苑》—般被看做是杂史,其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大大低于《史记》。

但这并不能说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为与《史记》相左就完全摒弃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迹颇多,司马迁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遗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说苑》是刘向根据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已散佚,只在《说苑》中保留了一点遗文琐语。
从这方面讲,《说苑》的确值得珍视了。
再者说,刘向所处的西汉与秦始皇时代相距不远,西汉人所记述的秦始皇事迹该不会有太大的走样与讹误。
加上西汉后期的人对秦始皇已不像汉初人那样憎恨,不会排斥在一定的场合下提及并且认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质的行为。
刘向或许正是掌握了这则资料,并且在编撰《说苑》时用上了。
秦始皇真的想过禅让吗?《说苑》中的内容是司马迁写史时所遗漏或有意不用的内容吗?由于还没有更多的证据加以论证,还无法确定最终的答案,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应该给秦始皇的人品作一个新的评价,所谓的专制暴君竟还有如此深明大义的事迹。
只“焚书”未“坑儒” 对于秦始皇的为人,无论是贬是褒,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即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
然而,对于秦始皇臭名昭着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秦始皇并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术士。
那么,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网络配图 关于“焚书坑儒”,《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秦始皇建立政权以后,视天下苍生为刍狗,贪婪暴虐,滥施刑罚,弄得民不聊生。
特别是他为了控制思想,听从丞相的建议,尽烧天下之书,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当时有两个为始皇求长生药的人,一个,一个,两个人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因为灭了诸侯,统一了天下,就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
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
他还颁布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
如今大家因为畏惧,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致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
他竟然还用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如果大臣们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简)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让休息。
像这种贪权专断的人,我们不能为他求之药。
” 于是,二人脚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听说此事后,又因为有人举报咸阳的诸生中有人妖言惑众,扰乱老百姓的思想,于是,始皇下令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读书人,并且严刑拷打,令其互相检举揭发,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牵连进来。
秦始皇一声令下,这四百多号人遂被活埋于咸阳。
这就是发生于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关于坑儒之事还有一种说法:由于秦始皇把文字统一为大篆和隶字,引起国人的诽谤怨恨。
考虑到识字最多的是儒生,为了防止他们带着天下人闹事,秦始皇决定对儒生下手。
秦始皇先是广召儒士书生到咸阳当郎官,共召到七百余人,然后密令亲信在骊山硎谷的温暖向阳之处种瓜。
瓜成熟之时正值冬天,他又指使人上奏:“骊山竟然冬天长出瓜来了!”秦始皇假装不相信,令诸生前去察看。
诸生到谷中之后,正在辩论不休之时,忽然四面土石俱下,所有的人都被压死了。
骊山硎谷后来又叫“坑儒谷”,在汉代,这里叫“愍儒乡”。
有人考证,坑儒谷在今陕西省临潼西南部五里处,是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地况很符合这个记载。
“骊山坑儒”说仅见于初年卫宏作的《诏定古文尚书序》,而且也没有注明出处。
因此有人认为,骊山坑儒其实就是咸阳坑儒的误记。
但是,卫宏是东时期的着名学者,治学严谨,以他的治学态度,应该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错。
况且,《史记》记载的秦始皇咸阳坑生,与卫宏所记骊山坑儒在地点、人数、坑埋方式上都不同。
所以,有人认为,如果卫宏和司马迁的记载都是真的,那么秦始皇至少坑过二次儒。
需要注意的是,《史记》中提到这段时,用的是“诸生”而非“儒生”。
而“坑儒”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典籍中,此时距秦始皇死后已经一百多年。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的财政管家在着名的上,发表了一通宏论,大意是,儒生们只知而不切实际,,就像那些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
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为他,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主张。
基于同样的道理,秦始皇才烧掉儒生们的着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他们活埋也不任用。
(见《盐铁论》)之后,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明确地提出秦始皇“坑杀儒士”。
此后,《史记》中所说的“诸生”渐渐演变成“儒生”。
魏晋时期,伪书《古文尚书》中有篇“孔安国序”,序中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这大概是“焚书坑儒”一词的最早出处。
这一说法被后世广泛引用,流传至今。
还原真相 先来说“焚书”。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网络配图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
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陈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实。
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
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
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
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来用不同的政策。
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徕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

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
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李斯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着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
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
”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损毁。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烧书。
这种记载是:“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意思是说,当初军队攻下咸阳城后,萧何先行没收了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坐了天下后,从这些图书中获得了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等资料。
从这段话中中不难看出,秦始皇只不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将它们烧了,至少没有全烧了。
否则,萧何收什么?汉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烧掉前代所着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
其实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书都烧了,上层建筑也就全完了,统治的基础同样会受到极大的动摇,他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杀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
这一天,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
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不知超标的是哪位。
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
随后就发生了侯生和卢生逃跑,四百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
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术士不等同于儒生。
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
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的齐人少翁,等等。
网络配图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
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
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载的安期生就是着名的术士。
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
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
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至于“骊山坑儒”的历史记载,由于是个孤证,所以尚不能作为定论。
方士中可能有儒生 前面虽然论证了秦始皇并没有专门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准儒生呢?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坑生”之后,其长子谏道:“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
这些儒生(原文是“诸生”)都是学习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
请皇上明察。
”秦始皇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到遥远的北方边境,让他当的监军去了。
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记载秦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诸生”或者“术士”,扶苏在进谏时,则把“诸生”的意思解释得非常明白:“诸生皆诵法孔子。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儒生。
为什么同一本书记述如此混乱呢?可能是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混进术士的队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禄,不想却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
另外,方术之士多数也是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
更何况,一旦杀戮就可能伤及无辜,这些被坑的“生”中难免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儒生。
秦始皇“坑生”的行为对秦王朝的打击是巨大的。
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对当时人们研习“六艺”是个致命打击。
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还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
陈胜能够在一个月内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些儒生功不可没。
按理说,儒生应该是最维护君臣纲纪的一批人,此时却纷纷跟随陈胜造反,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焚诗书”式的文化专制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走上武装反抗之路。
同时也应该与一部分儒生被杀有关。
试想,假如秦始皇坑杀的都是些、招摇撞骗的方术之士,不会对儒生们产生那么沉重的打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会那么恶劣。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焚过书,但并非尽毁;发生咸阳的坑“生”事件,其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但也波及到儒生。
秦始皇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蛮横无理,他所作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那些真实存在的事情虽然不能抹去,但通过揭示其背后的真相,可以帮助我们后人看清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希望世人对秦始皇的误解由此篇开始化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