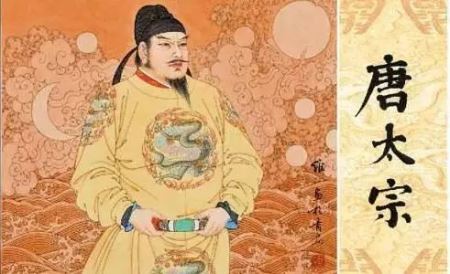汉武帝刘彻倾尽全国之力打匈奴,到底值不值得?
翻开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原农耕帝国与北方之间的恩怨情仇,一直是个永恒的主题。

如何跟游牧民族和平相处,是对中原帝国的一大考验。
处理不好与游牧民族这层关系的帝国,轻则带来严重的财政赤字,重则直接遭其侵略导致灭亡。
秦汉时期的北部边境形势 对待北方匈奴的办法是用武力解决,派大将修长城同时长期驻守北方。
当时的北方,存在多个游牧民族的政权,如月氏、匈奴、东胡。
统一天下的大秦,对游牧民族拥有绝对的国力优势。
但是,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中原帝国无暇顾忌草原。
这时候,匈奴单于东征西讨,破东胡、逐月氏;又向北降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一大帮草原政权;向南吞并了楼烦,甚至夺回了曾经被蒙恬大军侵占的河套地区。
莫顿单于统治下的匈奴基本上完成了对北方草原的统一,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汉初,经过”白登山之围“后,汉高祖意识到敌强我弱,不宜力拼,于是马上改变战略,采取了怀柔之术,通过送公主和亲和财物利诱,满足了匈奴的欲壑,实现了和平共处的安宁。
从此以后,惠帝、、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初期,虽然匈奴数次来犯,但对匈奴主要采取的都是和亲政策。
汉武帝时期,大汉对匈奴的政策开始转变 在韬光养晦几十年后,大汉的综合国力一跃千里,汉武帝认为大汉相比于匈奴终于不再甘居下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迎来了巨大的转变。
汉武帝对匈奴开始“磨刀霍霍”,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部署了著名的“马邑之谋”军事计划。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汉朝边境小城马邑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南下。
汉武帝出动了30万大军,集结于马邑附近试图伏击匈奴,另有一支偏师迂回草原,准备切断匈奴的退路。
不料单于率10万大军南下时,看到沿途牲畜遍野竟然无人照料,不禁起了疑心。
此时匈奴攻下了一处边防小亭,抓获一个地方尉吏,从他口中知道了汉朝的伏击计划,于是急忙北退。
马邑之谋就这样落空了。
从此匈奴与汉朝彻底翻脸,频频入塞侵袭汉朝。
马邑之谋中,虽然汉朝与匈奴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却酿成了巨大的外交事件,一举改变了亚洲东部两大强国间几十年来相对和平的态势。
匈奴断绝了和亲,并开始频频入塞劫掠,以示对马邑之谋的报复。
而汉朝既然已经踏上了选择战争的道路,汉武帝决意继续走下去,对匈奴转守为攻。
此后,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将整个中原王朝和草原力量都卷入了进去。
战争的本质,就是撒钱 战争的本质是国力的比拼。
这种比拼不是你掏出钱包来给我看一眼,说你有一百块钱,我掏出钱包来给你看一眼,有二百块钱,然后就宣布我赢了,我们两个都把钱包各自揣回去。
真正的战争是:你掏出一百元来,当场掏出打火机点了,问我:“服不服?”我,掏出二百块钱点了,问你:“不服,咋地?”就这么你来我往,直到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服软了,觉得再拼下去都得崩溃的时候,大家才坐下来和谈,结束这场战争。
所以,战争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游戏,一旦败了就一无所有,因此,上了场你就得玩命。
匈奴人都是作战,马匹的速度、冲击力、负重和耐力都是人类的数倍,马匹还拥有一定的智力,可以在奔跑中自动寻找合适的路径。
在的时候,还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
更妙的是,马匹吃草就可以维生,在北方的草原上,相当于拥有了取之不竭的能量来源。
因此,马匹在北方就是一台不需要加油的战车,还能成倍提高战士的速度和力量,简直就像是的神级武器。
面对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骑兵拥有绝对的优势。
有两个原因: 一、北方草原到处是牧草,是马儿的天堂,所以,马匹数量和质量都很高。
游牧民族的人又都从小都生活在马匹上,骑射技术是农耕民族比不了的。
二、游牧民族不需要种地生活,他们不用被束缚在土地上,可以轻易地举家迁移。
在对农耕民族的战斗中,游牧民族可以把全族的战斗力集中在一点上,任意袭击农耕民族的薄弱环节。

在得手或者失利的时候,可以随时撤退,不留恋一城一地的得失。
在敌人穷追不舍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可以深入北方腹地,在广阔的原野上和玩起捉迷藏,等到追击者人疲马乏、粮草绝尽的时候再杀一个回马枪,占尽地利的便宜。
农耕文明主要是步兵作战,面对这样有战力加持,又来无影去无踪的敌人,要想取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砸钱。
汉武帝选择的就是砸钱,花了七八年时间养了四十五万匹马,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
你有啥装备我就用钱砸啥,你的骑兵军团厉害,我就用钱砸出一支比你数量更多的骑兵团。
汉武帝打匈奴的高额成本 养马的成本 一匹战马的体重一般都超过一吨,所以每天需要摄取的能量是巨大的。
而且动物吃进肚子里的食物中,会有90%的卡路里会被浪费掉,而草中的能量又十分有限,所以一匹马每天要吃很多的草才能维持新陈代谢所需的能量平衡。
因此,游牧民族不得不经常四处迁徙,因为一片草场的草很快会被吃光,根本养不活他们那么多的牲畜。
在长城以北,马儿吃着几乎无尽的天然草料,养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马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就是相当于一辆自行车。
汉武帝要想养马就需要有广阔的草场,而对于古代农耕帝国来说,要养活庞大的人口,土地本来就不够用,怎么可能将大量土地变为草场,去养马呢?汉武帝要想发展骑兵,就必须另辟蹊径,将草料换成精饲料。
在食草的牲畜中,马是最挑食的。
什么麦子杆、高粱杆,牛会很开心地吃,马儿却一口都不吃。
马喜欢吃的是豆类这种人吃的食物,这就相当于人口夺食。
一匹马一顿顶几个人的饭量,这些豆子的种植又要消耗人力,战马每天还要参加大量的训练,消耗能量更多也意味着吃得更多。
里外相加,用精饲料养一匹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长城以南养马不光饲料消耗大,那些平时养在马厩里的马儿,要想锻炼奔跑,还需要开辟专门的跑马场,需要专人训练。
所以说,骑得起马的,那都得是“开宝马”的土豪。
饶是这样,汉武帝还是倾天下之财,养了四十五万匹战马。
汉军深入匈奴人腹地作战的高额成本 汉武帝跟匈奴人打的那场最大的胜仗,汉军出动了约十四万匹战马,损失了约十一万匹。
一场大胜仗都损失成这样,那一般的战争还怎么打?打完仗,人家游牧民族回去随便找一个牧场,养几年,马匹又都出来了。
你汉军回到长城内,还得花费巨资重新养马。
更严重的是,深入草原作战,后勤补给的成本更是高的吓人。
一般骑兵作战,后面是步兵负责补给。
汉武帝的几万骑兵远征,要配备几十万的步兵补给军团。
为啥要这么多人,因为人少了根本守不住这么多粮草,一旦补给被切断,前面冲锋的骑兵也就玩完了。
问题是,这几十万人也要吃饭啊。
所以,汉武帝是靠多支出了几十万人的人力与口粮来解决补给问题。
古代运输成本极高,按照司马迁的记录,汉朝给西南边境运送粮食,运输成本高达六十多倍。
时从山东地区运粮到内蒙古,运输成本高达一百九十多倍。
而汉武帝北征,距离更远、路途更艰苦,运输成本还会更高。
哪怕就按六十倍计算,这也意味着汉武帝一下子就要往大漠里扔进去最少几千万人份的粮食。
这个数字太恐怖了,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也不过几千万人。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挂帅奇袭祁连山,杀死和俘虏了匈奴士兵共计三万多人,擒获了匈奴的单桓王和酋涂王等五个大王,以及他们的王母、王妻、王子共计五十九人,擒获匈奴的相国、将军、都尉六十三人。
袭击祁连山这一天,成了匈奴国的“哀悼日”。
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匈奴发出了这样的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汉军拿下河西走廊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刘彻 梦骏马生渥洼水中 ,大臣作天马歌献上。
即刻下昭在中央王朝设苑马寺负责马政,在大马营草原设置牧师苑。

大马营草原因位在河西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中部,且这里有天然大草场和丰盛的水源,历朝王师大军从这里不断得到军马补充,这就是山丹军马场。
有了山丹军马场(今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帝国的财政压力才逐渐地得以缓解。
结语 前文说过,战争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游戏,虽然从人类整体上来看,战争是一个负收益的行为,但是站在发动战争者的角度看,战争有可能是划算的。
只要战争预计的成本小于预计的收益就行。
换句话说,在战争的发动者面前有一个财务表,一边写着这场仗预计花多少钱,另一边写着万一咱赢了能赚到多少钱。
只要后者比前者大,就有发动战争的理由。
匈奴是大汉帝国在北方的国防安全隐患不假,汉武帝打击匈奴以固国防,这没问题。
但是,你也得算计下收益和成本啊。
汉武帝如果能计算清这成本,在汉军拿下河套地区以及打通河西走廊后,就应该转攻为守了。
因为这时候汉军以及掌控了匈奴人南下的战略要地,匈奴已经对长安构不成威胁了。
但是,汉武帝固执地想完成前人未成之壮举,就是彻底消灭匈奴以绝后患。
所以,他多次组织远征军深入大漠。
可事与愿违,即使你这些战役打胜了又能怎么样? 北方太大,游牧民族又善于迁徙,只要暂时避开汉军的刀锋,等到汉军退兵后再找一块肥美的草原,就可以恢复生机,没几年匈奴人又能。
因为,你汉军不可能长期在草原驻军。
由于降水少,草原地区的不适合耕种,所以,汉军驻军后只能像匈奴人一样游牧化。
手握重兵居无定所,时间一长,汉军岂不胡化?把匈奴人赶跑了,却无法长期有效地统治他们的土地。
因此,汉武帝即使撒再多的钱,也无法彻底消灭匈奴。
对汉朝来说,要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分化瓦解匈奴,用一个草原部落来制衡另一个草原部落,从而保障长城以南的王朝疆域内的长久和平。
你消灭了匈奴又能怎么样?匈奴没了,还会有其他游牧民族部落崛起。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对匈奴大规模用兵,派利等率领十几万大军多路出击,试图武力彻底征服漠北的匈奴。
匈奴单于把辎重转移到鄂尔浑河以北,自己在鄂尔浑河以南率领匈奴大军,迎击汉军。
这场战役以汉军大败,投降匈奴而告终。
至此,汉武帝想生擒单于、根绝匈奴之患的愿望彻底破灭。
而且国内民怨四起,长安城外盗寇盈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江山社稷摇摇欲坠。
一个合格的国君,他的职责是要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去选择净收益最大的那一种国策。
拿下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已经是与匈奴作战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如果这时候汉武帝能收手,汉朝对匈奴的作战是非常值得的。
但是,汉武帝选择继续向北打下去,这时候的战争的边际收益逐渐减少到了负值,甚至可谓是耗尽家财,这显然不一笔好买卖。
汉武帝为了消灭匈奴,将“”留下了老本折腾没了,又施行货币垄断、盐铁专营、酒榷、算缗告缗、卖爵等敛财的政策来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
这些政策榨干了民力,破坏了帝国的经济结构,也让大汉帝国开始走向衰落。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汉武帝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轮台诏》,后悔派遣李广利远征带来军事上的惨败,宣布国家将从横征暴敛、连年征战转向休养生息、和平发展。
这也是他对自己倾尽国力征伐匈奴的一个回应。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带着未能歼灭匈奴的遗恨去世了,汉朝北部边境的匈奴仍然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南下侵扰大汉边境,始终刺激着汉武帝后世子孙们的神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