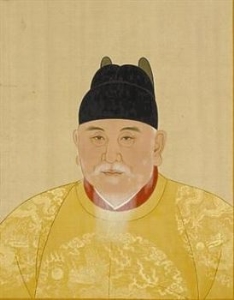阮大铖这个人,中国的知识界几乎人人皆知。
然知道他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他是个著名的奸佞之徒。

说阮大铖是奸佞之徒,实在没有冤枉他。
此人44年中进士,熹宗天年间任吏科都给事中,后依附阉宦,很做了些坏事。
崇祯时被贬斥,虽企图,都受阻于和复社,前后长达17年。
到南明弘光时,他又依附权奸马士英,任兵部尚书,又做了大量坏事。
清兵攻打金华时,他主动乞降,成了民族的罪人。
但是,阮大铖又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诗写得很好,文章也上乘,著有《永怀堂全集》。
特突出的是写戏,有11种传奇(剧本)行世,现有的尚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多部。
这些剧本,一经演出,就极受群众欢迎。

明末大文学家张岱在《阮圆海戏》里,说他的作品:“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笔笔勾勒,苦心尽出……本本出色,折折出色,脚脚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特别是《燕子笺》,写书生梁与青楼女子华行云及官府小姐郦飞云之间的爱情故事,其观点就很值得称道,加上情节委婉有致,唱词清丽可人,是中国古典剧目中数得上的好戏,连他的政敌复社的陈员慧、侯方域也交口称赞。
《明史》尽管把他列入“奸臣传”,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剧本“脍炙艺林,传布最广”。
对于阮大铖这样的人物,几百年来,人们对他似乎过于的严酷了,严酷到“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叫他永世都不得翻身”的地步。
应该说,在政治上,道德品节上对他严酷是对的,但不能因为其是奸臣,是民族罪人,就连人家明明是大戏剧家也都不予承认。
据说在年间某地曾上演《燕子笺》,虽然受到群众欢迎,后因为知道是阮大铖所作,被禁演了。
解放后,我们出版了那么多的文学史、戏剧史,大多数根本不提阮,个别提到的也只是一二句而已。
现在,青年人绝大多数已不知道三百年前,中国尚有这么一个大剧作家了。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太严酷,完全可以啥事按啥说,不要死抱住那个“文如其人”的老框框不放;不要认为:人坏了一切就都坏了。
历史上文不如其人,诗不如其人,画不如其人的多得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不能因人废言,更不能因人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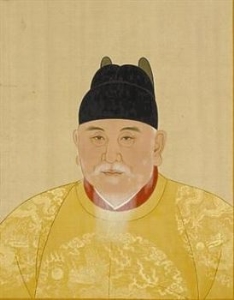
还有个奸臣叫,写得一手好书法,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奸臣就连人家书法家的资格也不承认了。
文章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周作人。
要说他政治上的反动和为人的卑劣,比阮大铖坏多了。
阮大铖当年迫害东林党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他的降清,说到底是这一朝降到那一朝,是中国降给了中国人。
可周作人就不同了,他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难当头时,他给日本人办事,是名实相副的汉奸、卖国贼。
但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因周附逆当汉奸而否认其为大作家。
他的作品出了又出,印了又印,甚至有人因为他的作品而讳言其汉奸身份。
从这点看,同样是奸佞,我们何厚此而薄彼,这不是很大的不公平吗? 看来,还是用两分法的态度对阮大铖为好,给他一点宽容,承认他是中国大戏剧家之一为要。
今年是阮大铖先生辞世355年,能不能给他出一本戏剧集,以证明他的存在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国古时候历史上最奇葩的帝王高从诲,喜欢当强盗,抢完还把东西送回去
夏日,荆南某地。无风,日头很毒。 几处起伏蜿蜒的丘陵上,稀疏的草木蔫得抬不起头来,没有一点生气。丘陵外是一片开阔的原野,干裂的地缝中似乎要翻滚出热浪。 身体略胖的高从诲即使在背阴处也是汗流浃背,不得不敞开衣襟。随从拼命地给他扇着扇子。50多名劲装汉子也都热得下了马,地提不起半点精神。战马也蔫耷着耳朵,失去了往日的雄威。 蓦地,远处隐约出现了几个黑影。 是一列马队! 这是楚国去往吴国的使节所率领的马队。车上的货物显然很重,马拉得很吃力。 高从诲眼睛一亮,立刻。他一边招呼着部下,一边兴奋地搭手瞭望。 马队由远及近。高从诲大叫一声,旋风般地第一个冲了出去。 马队中的人没有反抗,因为他们知道反抗也没有用,他们已经猜出领头的响马是谁了。 这已是高从诲第十五次实施习惯性抢劫了。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爱好。 但是谁能想到,这个在烈日下当“响马”的人,居然会是堂堂的一国之君-时期南平国的文献王! 高从诲有当“响马”找乐子的癖好。有这种另类癖好的,在中国历史上绝难找出第二个。尽管先前14次抢劫之后,在各国的责难下,高从诲已经把抢到的东西原物奉还,并且还向各国赔了礼道了歉,但这次他仍旧没能经受住这种习惯性的诱惑。冒着酷暑,做完这第十五次“买卖”后,他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朝。 高从诲生于891年,其父高季兴原为后梁时的荆南节度使。912年,被其儿子朱友珪诛杀,后梁大乱,高季兴趁机自立,割据荆南,定都荆州,国域范围包括荆、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是个地域狭小的小国,被后梁、楚、蜀、吴国所包围,处于夹缝生存状态。 高季兴死后,高从诲即位,在933年被后梁封为渤海王,次年又改封南平王,因此荆南国也叫南平国。 高从诲“为人明敏,多权诈”。据《五代史》记载,顺化节度使安从进起兵反晋,想与荆南国联手,高从诲不敢得罪后晋,“外(表面上)为拒绝,阴(偷偷的)与之通”。等后晋的大兵压境,高从诲见势不妙,便,灭了安从进,“晋师致讨,从诲遣将李端以舟师为应”,然后又向晋国讨功卖好,讨要郢州(今湖北钟祥)之地。 高从诲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他的“响马”嗜好了。他专门以掠夺途经本国辖区的各国使节为乐,《五代史》记载:“从诲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一旦他国致书询问或是发兵征讨,他又会忙不迭地将原物奉还,脸上毫无愧疚之色,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南方俗语管这种人叫“赖子”,于是周边诸国都管他叫“高赖子”。因为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别的国家也就见怪不怪了。更雷人的是,周边国家不管谁称帝,他都“所向称臣,盖利其赐予”。 这还真不是个一般人。 贵为一国之君的高从诲,为何有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当“响马”的嗜好?估计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帝王骨子里都有征服的欲望。荆南国小力寡,不能与他国抗衡,高从诲的欲望自然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出来客串一下“响马”,威风凛凛地抢劫一番聊以慰藉,也算过过王者之风的瘾。二是内心的一种发泄。高从诲在夹缝中生存,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心中不免压抑,实在憋屈不过了,便通过抢劫的形式以作发泄。 不管是高从诲委曲求全也好,自我慰藉发泄也罢,在他在位的19年里,荆南国国境承平,百居乐业。这在晦暗的五代十国时期也算相当难得了,也许这正是他“为人明敏”的一种体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为什么古时候帝王动不动就爱抄大臣家籍没家产?
此页面是否是列表页或首页?未找到合适正文内容。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