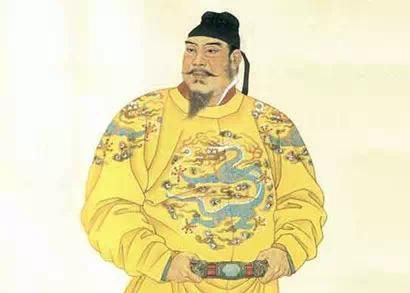张汤是西汉酷吏,他曾得到汉武帝刘彻的赏识,地位也是水涨船高。关于张汤是忠臣还是奸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有一些争议的,可能不能简单的做出评判。那张汤曾帮助汉武帝刘彻推行盐铁专卖,打击富商,剪除豪强,因此颇受信任。但张汤最终结局并不好,他是遭到诬陷,导致被杀。今天就借此机会,和各位讲讲张汤的故事,看看他究竟是一个如何样的人,好奇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

攀龙附凤
小张子承父业“为长安吏”,深知如果按照正常晋升程序,熬到退休也混不出名堂。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剑走偏锋,出奇制胜。
正巧,九卿之一的田胜因违法乱纪被朝廷逮捕关押在长安。小张得知他是当朝丞相田蚡的亲弟弟后,使尽浑身解数,上蹿下跳为他洗脱罪名。田胜在哥哥暗箱操作和小张的极力洗白下得以安稳 出狱,并因祸得福获封周阳侯。他知恩图报,亲自带小张拜访长安权贵,“遍见贵人。”田蚡又征召他为丞相史,继而推荐他给汉武帝刘彻担任御史,专司处理诉讼案件。
张汤首秀非常成功:陈皇后失宠后心理失衡,竟然唆使女巫以巫术诅咒汉武帝刘彻。东窗事发后,汉武帝刘彻震怒,定性为“陈皇后巫蛊案”,交有司彻查。张汤穷追猛打,刑讯逼供,最后将涉及此案的嫌犯一网打尽,以此被晋升为太中大夫,并“与赵禹共定诸律令”,一跃成为朝廷法令的制定者,登上一个更能大显身手的舞台。

法律专家
张汤因汉武帝刘彻偏爱儒学,遂投其所好,奏请研习《尚书》、《春秋》的博士儒者补任廷尉史,以便遇到有疑问的法律条文时,请他们依据《尚书》与《春秋》的思想原则予以评断,使之符合儒家思想。此举深得汉武帝刘彻欢心,视其为股肱之臣。
张汤上奏疑难案件时,总会预先向汉武帝刘彻说明断案原委。凡是被汉武帝刘彻肯定的做法,他就明确规定以此为法律依据,以显示帝王英明。一旦奏事受到汉武帝刘彻斥责,他总会花言巧语为自己辩解。
他善于揣度圣意,以汉武帝刘彻的好恶当作判案依据。如果汉武帝刘彻有意除掉某罪犯,张汤便立即令下属深挖余罪定死刑;如果汉武帝刘彻有意宽宥某罪犯,张汤便指示下属挖空心思从轻发落。
张汤判处豪强毫不手软,审理平民则相对宽大。他对待高官小心谨慎,一视同仁善待旧友子弟,遵照礼节拜见公卿。因此,张汤断案虽然不算很公正,但他的一些做法还是获得称誉。因此,他的粉丝既有像他一样的酷吏,也不乏品学兼优之人,丞相公孙弘就曾“数称其美。

双面人生
张汤在奉诏处理三王谋反事件时,排除阻力一查到底。汉武帝刘彻认为涉及案件的严助和伍被人才难得,指示张汤网开一面予以释放。张汤坚决原判:“严助图谋不轨,千方百计亲近交结出入皇宫的陛下近臣。伍被更是为淮南王谋反出谋划策。此二人必须严惩,以儆效尤!”汉武帝刘彻被说服,同意判处二人死刑,并将张汤晋升为御史大夫。
张汤在审理案件时的确有几把刷子,凭借聪慧才智侦破过不少大案要案。但是,帆叶网,在此过程中,他也趁机排挤涉案大臣,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他还善于玩弄智谋驾御他人,“为人多诈”。因此,他在踩着同僚尸体步步高升的同时,也埋下失败的种子。
时值“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苦百姓流离失所,全靠官府救济。汉武帝刘彻为解决官府库存空虚现状,有意垄断市场以充盈国库。张汤对汉武帝刘彻的心意心知肚明,主动跳出来“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为配合政策顺利实施,张汤还以法律形式颁发“告缗令(动员民众交纳税收和揭发偷漏税的法令)”。
汉武帝刘彻还与张汤研议发行所谓"白鹿皮币",规定亲王贵族至长安朝觐帝王时,必须购买一张价值四十万钱的白鹿皮币。颜异时任大司农(相当于今财政部长),坚决反对这种变相勒索敛财方式,惹得汉武帝刘彻极为恼火。适逢有人诬告颜异持不同政见,汉武帝刘彻遂将其交由张汤处置。张汤审不出结果,索性以莫须有的“腹诽罪”判处颜异死刑。
从此,丞相成为摆设,“天下事皆决于汤。”张汤主持的财政改革使得“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官府主持的生产部门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无法获利。官吏们又习惯吃拿卡要,难免雁过拔毛侵吞渔利。张汤采取严峻刑罚,把这些人严格依法惩办,导致“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都对张汤满腹怨言。但因汉武帝刘彻将张汤依为臂膀,只能忍气吞声,静待时机。

明枪暗箭
张汤最初担任长安小吏时,曾利用职权与商人们合谋取利,与长安富贾田甲等人暗中往来密切。田甲虽只是个生意人,却“有贤操”。张汤发迹后,田甲曾多次当面义正辞严指责他“行义过失。”张汤倚仗汉武帝刘彻宠信,置若罔闻。七年后,终于因民愤极大,被罢免御史大夫职务。
以李文为首的政敌们立即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挖空心思企图从他的奏章中找到黄色反动的文字,都未能得逞,于是改变目标,企图从张汤的亲信下手找到突破口。
正巧,张汤的心腹鲁谒居为了拍主子马屁,唆使他人上奏揭发李文图谋不轨。汉武帝刘彻为考验张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张汤清楚这是心腹鲁谒居在表忠心,顺水推舟将李文判处死刑。他得知鲁谒居患病后,亲自探访,并其按摩双足。赵王将此事告到朝廷,怀疑二人有阴谋。汉武帝刘彻终于对陈汤起了疑心,令廷尉彻查此事。
鲁谒居因病重一命呜呼,连累其弟被逮捕入狱。张汤企图为他开脱罪名,便在审讯时假装不认识,公事公办。鲁谒居的弟弟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怨恨不已,破罐子破摔上书告发张汤与哥哥有阴谋,同时诬陷李文等大臣图谋不轨。汉武帝刘彻大怒,指示将此案移交酷吏减宣处理。
恰在此时,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被盗,丞相与张汤相约同往金殿谢罪。当丞相向汉武帝刘彻谢罪后,张汤自忖此事纯属丞相失职,与自己没有一毛钱关系,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汉武帝刘彻命令御史彻查此事,张汤落井下石,奏报丞相知法犯法,吓得丞相魂飞魄散。丞相府三位长史忍无可忍,决定联手除去张汤。
三位长史都是先前地位高于张汤的前辈。张汤为小吏时,见到他们即行跪拜之礼,飞黄腾达后,时常故意羞辱他们。他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于是合伙谋划:“张汤与丞相相约向皇上谢罪,却转身出卖丞相;现在又欲以宗庙之事弹劾丞相,这是明目张胆企图取代丞相!我们必须揭发他!”

他们说干就干,立刻逮捕审讯张汤的友人,刑讯逼供逼迫他们承认与张汤勾结囤货居奇获取暴利。汉武帝刘彻面对供词满腹狐疑:“张先生,为什么朕有何打算,商贾们都了如指掌,趁机囤货居奇?显然,必然是朕的身边人与他们相勾结!”张汤自认为光明磊落,根本不做辩解。汉武帝刘彻却由此陡然生疑,派酷吏减宣以八项罪名质问张汤。
宣素与张汤不和,趁机公报私仇,威逼利诱他认罪伏法。张汤却气定神闲,坚决否认八项指控。张汤的老上司赵禹奉诏诱供,面责张汤:“这么多年来,经过您手审讯被处死的人,不论有罪无罪,至少成百上千!如今您的罪名证据确凿,皇上很想给您一个体面的谢幕机会,您如何如此不开窍?”
张汤终于明白,唯有自杀才是唯一解脱方法,于是上疏谢罪:“张汤无尺寸的功劳,从一个小小的刀笔吏起家,承蒙陛下恩宠,得以位列三公!但是,臣的忠心苍天可鉴,所有对臣的指控均属无中生有!设计陷害臣者,便是丞相府三位长史!”写完后,张汤“遂自杀。”
张汤死后,遗产不到五百金,且均来自皇上恩赐,没有任何不正当收入。张汤的侄儿想要厚葬他,被张汤之母制止:“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老太太用牛车装载张汤的遗体下葬,“有棺无椁。”汉武帝刘彻闻之深受感动:“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且令将三位长史判处死刑,逼得“丞相青翟自杀。”
张汤是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说他贪赃枉法似不为过,但死时清廉到遗产不足五百金;说他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他又敢坚持原则顶撞皇上;说他是令人痛恨的酷吏,他又扫黑除恶同情百姓;说他利用职权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又毫无私心一心一意为国家敛财:说他排除异己妄自尊大,他又不结党营私危及皇权。
也许,真正有血有肉的立体人物,才是古代中最真实的影像!因此,张汤究竟是大奸似忠的酷吏,还是刚正不阿的贤臣,后人只能站在自己立场上见仁见智!
【作者简介】许云辉,男,1984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省保山一中教育集团高级讲师。曾出版专著两部,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文章六十余万字。
丁谓为什么会上佞臣榜而寇准却上了忠臣榜呢?
之所以能登上佞臣榜,仅仅因为一个人,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寇大人;而其间的因缘际会,仅仅因为一件小事,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溜须”事件。 关于溜须事件,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天禧三年(1019年),三起三落之后的寇准再度出山,取代成为宰相。也就在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也再次升官进入中书省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二人成为同事,关系也非常亲密。寇准曾多次向担任丞相的进士同年推荐丁谓,但被李拒绝。寇准问其原因,李回答说:“看他这个人啊,能使他位居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能始终压抑他屈居人下吗?”然而,有一天,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后,身为内阁成员的寇、丁二人都参加了宴会。宴会间,寇准的胡须上沾有一些饭粒汤水,身旁的丁谓见了,起身上前替他徐徐拂去。这一举动在同事兼好友间,自是常理也合常情。可是寇准不以为谢,反而板起了脸,冷笑着说了一句让丁谓下不了台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网络配图 那么,丁谓为什么会上佞臣榜,而寇准却上了忠臣榜呢? 先来看丁谓这个人吧。 丁谓的遗憾也许就是现代人的遗憾,现代人的遗憾也就是寇准的遗憾。 丁谓,字谓之,后改为公言。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966年,正牌的进士。丁谓年少的时候就以才出名,当时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看到丁谓寄来的作品后大惊,以为自唐、后,二百年来才有如此之作。可见他仕途起点之高,令人头晕,也就不足为怪了。淳化三年,也就是初登进士甲科之时,就担任了大理评事、饶州通判,相当于副省长。只过了一年,就调回了中央,以直史馆、太子中允的身份到福建路(北宋废“道”为“路”,初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设,后逐渐带有行政区划和军区的性质)去采访。回来之后,就当地的茶盐等重要问题写了篇调查报告,引起了的重视,当上了转运使,相当于节度使,并且还兼职三司户部判官。不过,由于派系斗争的传统,丁谓仕途后来也有起伏。 丁谓的才干,其实远在寇准之上。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个“一举而三役济”的故事,说的就是丁谓。大中祥符年间,禁宫失火,楼榭亭台,。命晋国公丁渭担负起灾后重建的重任,修葺宫廷。丁谓采取了“挖沟取土,解决土源;引水入沟,运输建材;废土建沟,处理垃圾”的重建方案,命人将街衢挖成壕沟以取土,再把水引入壕沟,以便将城外的建材通过水路运进城中,等房屋建好后,那些壕沟又成了废墟垃圾的回填场所,不仅“省费以亿方计”,还大大缩短了工期。这样精巧的规划、缜密的思维,即使是现代都市的规划师也未必想得到,只要看看城市里的马路有人恨不得装条拉链就知道了。网络配图 再看他另一件大事。丁谓官拜副相之后,四川一带发生了以王均为首的少数民族叛乱,中央先后征调大批兵马前往平乱,都被叛军打得。丁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深入蛮地,竟然以兵不血刃之势,安抚了叛乱。 接下来看看寇准。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比丁谓大五岁,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寇准之所以能,其实也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中学课本里讲的“”。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宋真宗渡河亲征,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势。《》上提到寇准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正直”。不过,说他“直”,没话讲;说他“正”,就值得重新考量了。 “澶渊之盟”后,有人对皇帝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皇上听说过赌博吗?赌博就是倾其所有,寇准就是把您当作他的“孤注”啊。这个比方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当时的中央并没有势力和辽国抗衡,会盟前,寇准曾经威胁和谈代表,说要是超过了某某数,就要砍他的头。想来皇帝听了这话,心上一定会隐隐作痛吧。 寇准一生为官远不止“三起三落”,但都是因其不“正”而导致的。仗着“澶渊之盟”有功,寇准的权力欲达到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实行宰相专政,常常居高临下地左右皇帝。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依制度不应由宰相插手的御史任用上,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规定,“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当时中央流行着一种偏见,瞧不起南方人,寇准也终生瞧不起南方人,一直排斥南方人。景德二年,14岁的以神童召试,时任宰相的寇准因为他“(属)江左人”,也想压制他。所以后来丁谓偏要把他贬到南方之南的雷州,让他病死在那里。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的力荐下,寇准重回权力之巅,任西府枢密正使。两个人本来应该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态度与王旦共事,而是不时地给他找些麻烦。史载:“(寇)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王)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就是说,寇准对东府送来的文件,总是要地找差错,找到了,并不与东府商量,直接呈报给皇帝,借皇帝来责罚王旦,有意出东府的丑。 一报还一报,后来,东府的人也有样学样,凡西府送去的文件,他们也找岔子,以报复寇准。但王旦却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直接把文书退给了枢密院,没有报告给宋真宗。当枢密院吏把这件事汇报给寇准时,寇准感到非常惭愧,第二天,见到王旦,对王旦说:“王同年大度如此耶!”网络配图 王旦的行为虽然让寇准感动不已,但寇准还是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攻击王旦。他的行为与后来王旦处处保他相比较,真是“复复何言”。 当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点的官(使相)。对于寇准这种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深恨之”。但当宋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后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 王旦为相12年,病重之际,宋真宗让人把王旦抬进宫中,问以后事:“卿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开始并不直接回答宋真宗的提问,仅说:“知臣莫若君。”宋真宗没办法,只好一一点名来问,王旦都不表态。最后,真宗只好请王旦直说:“试以卿意言之。”王旦这才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但宋真宗对寇准的性格不满意,说:“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这时,王旦固执地坚持:“他人,臣不知也。” 然而,这一次,寇大人一上来就碰上了丁谓这样一个才气和才干都比他高的对手。寇准在和丁谓的争斗中,因为看不起刘皇后而得罪了她。担心自己的处境,寇大人决意发动政变。然而,机事不密,一次,自己走漏消息,被丁谓的亲信觉察到了,很快寇大人就走上不归路,曾被寇准压制过的等多人纷纷出了口恶气。半年后,真宗还念念不忘:“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 莫名其妙的是,“多致人言”的寇大人竟然也能名垂青史!唉,说到这里,不得不叹,有些事情,原本就不该这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酷吏张汤 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御史大夫张汤因何而死
酷吏张汤: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而张汤就是其中十分出名的酷吏之一。那么张汤又是因何而死呢?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